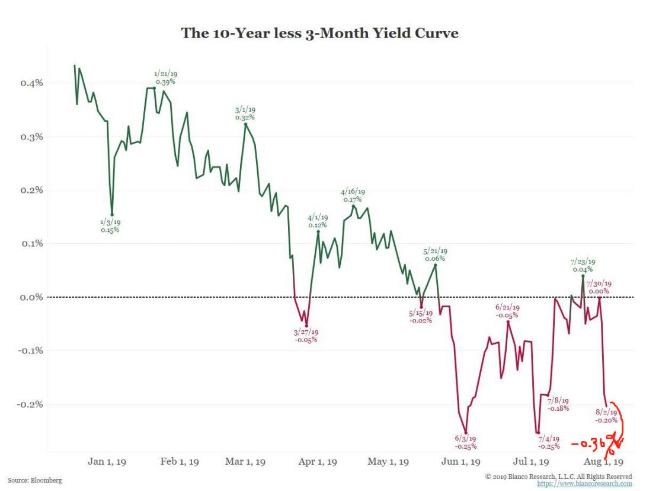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如何做到权威且有效的?
2017-12-01来源:中国南京网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确立于秦汉,至隋唐臻于完备,历经变革延续至晚清,可谓源远流长。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十分重要,纲纪之整肃、吏治之维护、政治污弊之涤荡多有赖于此,是公正、有效之政治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保障。
从御史与谏官之间关系来理解,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系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时期形成了御史与谏官并存的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隋唐时期御史与谏官相辅相成,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宋以后谏官制度逐渐衰微,及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御史与谏官制度合一的、以督察院为主体的单一监察制度体系。
从复合性制度体系到单一性体系的演变,不仅是制度性的改变,更是监察制度理念的蜕变,从此种蜕变中后人可以深切体会到古代监察制度的君主工具性价值和天下整体性价值的整合与分裂。
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足以震慑权贵
无论是复合性体系,还是单一性体系,监察制度的权威性均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监察权本于天道,又以现实法律(惯例)为其依据,体现了天下整体性价值,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监察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为“史官”之一种,谏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秦统一后所建立的监察制度,虽然历经改造,但是监察官仍以天下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任。监察官对上级负责,对君主负责,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利益负责;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监察官依据法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被其监察的高官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国古代的盛世善治,大多是监察制度运行最好的时代,例如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得益于君主奉法而治,监察官严明职守,正如《通典·职官六》中所称:“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唐太宗曾盛赞著名谏臣魏征:“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其二,复合性的体系设计,御史与谏官相互配合,中央与地方一体,监察制度覆盖所有的权力领域。御史职掌监劾臣僚,是上对下的监察;谏官职掌匡正君主违失、封驳失当政令,是下对上的监察。御史与谏官上下相对、相辅相成,既可以构成监察的合力,又把君臣之权全部纳于监察体系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一体的监察体系,历代都极为重视监察御史,对朝官、京官的监察与对地方官的监察都由独立而统一的机构来行使,各个地域的权力都在统一的监控之下。
其三,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之具有超越于被监察者的权威性,足以震慑权贵。御史和谏官大多是服务君主的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官,保留了侍从君主左右或奏章直达君主的特权。他们在监察朝官、京官或是巡察地方时,均为君主的代表,其官品虽低却独立行使职权,直接对君主负责。御史在行使纠弹权力时,奏章可以直达君主;对于重大事项,可以晋见君主,面陈奏章。为避免职务干涉,御史甚至可以绕过御史大夫等御史台长官,直呈君主。御史台长官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内。御史为保护举报人,避免被纠举人以权势威胁举报人,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其权威性足以纠察官邪、肃正纲纪。
监察官员大多“位卑、权重、厚赏”
自秦朝以来,无论是御史还是给事中等谏官,选人条件明确,纵然君主也不能以个人好恶而任意用人。历代选任御史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不无共同之处,“通常以学识、德行及政治经验三者,为遴选御史的评价标准”。监察官之学识首重律令知识,次重官吏职守及相关政治、经济知识,便于其能究明法律责任,判断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履行职务的绩效。监察官之德行须以效力国家社稷为己任,爱惜名节,不受权力与利益之诱惑,且勇毅刚正,不畏权贵。出任监察官者必须有三年以上担任其他官吏的经验,如无经验,须经试用合格方能任职。总此学识、德行、经验三项任职条件,监察官多为德才兼备之干城。
“位卑、权重、厚赏”的理念,源自法家对监察官的职位设计,秦朝之后沿袭不替。汉朝的御史大夫秩二千石,而巡视地方的刺史仅为六百石;唐朝的御史大夫为正三品,巡视各道的监察御史仅为正八品;明清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监察御史仅为从七品。历代监察官员都延续了“位卑权重”的特点,正是因为位卑,可以因弹劾之功获得厚赏,可以越级擢升,并且晋升空间极大,既可在监察系统内晋升,也可以转为其他系统的职官。“厚赏”成为对监察官的现实激励,促使其竭诚尽忠于本职。
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对实现良好的政治法律秩序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莫不以良好的监察制度作为保障;明朝阉党柄政、皇帝昏聩,却能享国二百七十余年,其中不乏众多监察官竭力维系之功。然而,监察制度不可能超越整个政治法律体制,在抗拒社会各方面压力的过程中,纵然好的制度也会发生蜕变,逐渐丧失最初设计的制度理念与功能。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三方面的力量会消解监察制度的理念和功能,促使其蜕变:
其一,皇权对监察制度有着构建之功,也有侵蚀的危险。以汉朝为代表的台谏分置监察体系,以唐朝为代表的台谏相辅监察体系,都对君主起到约束、规谏的作用,但约束最高权力的监察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却深受君主个人的影响。在宋朝以后,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监察体系的整体性价值在衰退,工具性价值却在上升。
其二,有效监察地方权力的前提是能够超越于其上,不被其所牵制,又能深入于其中,同时不陷入其利益格局。可是能做到超越于其上、又能深入其中,是非常难以把握的。汉朝设置部刺史监察巡察地方,最后演化成了地方官;唐朝设置按察使巡察地方,也渐渐地方化;明清两代的提刑按察使、总督、巡抚都是从监察官转化而成的地方官,都失去了中央监察地方的制度职能。可见,超越于其上,深入于其中,在制度上颇难把握。
其三,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及其附属的御史和谏官,本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涤荡吏治污弊、实现公正的政治法律秩序而设置,可是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环境中,少数监察官或依附权贵,或为利益所诱惑,制度虽称良善却难达预期。监察官的监察为历代所重,而监察者又须被监察,不免造成机构的重叠、国家治理成本的上升。
上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值得我们当今监察立法、构建监察体系借鉴;另一方面,古代监察制度的蜕变也值得注意,避免制度虽立,成效不彰。